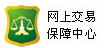回归计划经济的话语开始出现倒退首先表现在改革的话语上。中共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党章,之后又写入宪法,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问题早已经解决。但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纷纷出现市场经济怀疑潮。一些人,尤其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怀疑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并存,很多人把中国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归诸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解体了传统社会秩序,但没有能够产生新的社会秩序。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分化,社会道德严重衰落。这些都是改革前毛泽东一代领导人要解决的问题,并且也的确被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国社会出现很多很大的声音,否定邓小平路线,呼吁回到毛泽东。各种变相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话语,又出现在经济社会改革的话语中。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看,这并不难理解。在经济改革成为主体改革的年代,主导改革的都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他们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分野问题,或者说他们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政策上,没有能够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结果,在很多方面造成了社会政策的经济政策化;就是说,在一些本应当属于社会政策的领域,经济政策畅通无阻,甚至推至极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发生在经济领域,而社会领域是受国家保护的。但在中国则相反。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国有部门,因为有国家力量的抵制,新自由主义很难发生作用;但在社会领域例如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方面,新自由主义则大行其道,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现在当社会政策成为主体性改革的时候,人们不仅忽然发现,社会领域已经被市场破坏得体无完肤了,更重要的是,进入社会领域,尤其是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的既得利益已经变得无比强大,能够有效抵制政府的任何改革了。于是乎,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经济。再者,社会政策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因此凸现出来。很多人开始用社会政策的思维套用到经济政策上,怀疑经济领域的市场作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认知误区,那就是,社会改革者和经济改革者一样,没有能够区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正如社会政策不能经济政策化,经济政策也不能社会政策化。在经济政策领域,不能无限夸大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正如在社会政策领域不能过分夸大经济政策的作用。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存在矛盾实际上,在社会领域因为新自由主义入侵变得过度市场化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中国面临着的是市场化不足的问题。近年来,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仅没有深化,而且有减低的趋势。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部门。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和市场没有关联。朱镕基改革时代,在实现企业公司化和法人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日后改革没有能够深化下去。国有企业的行为仍然不是市场主导的。这表现在多个方面,主要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政府仍然视国有企业为自己的“自留地”,政府可以随意向其属下的国有企业提取利益;国有企业也仍保持着行政级别。尽管很多国有企业想放弃行政级别,但政府不想放弃,因为政府想用这一政治方法来控制企业。另一方面,既然国有企业不是单纯的企业,那么它们就要利用政治和行政权力来搞垄断,形成人们所说的权贵经济,或者权力市场。
今天的国企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下的国企,权力+市场是今天国企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使得国企能够在近年来急剧扩张,大量挤占民企的空间。这就是人们称之为“国进民退”的“国有化”现象。尽管有关方面不承认,但事实上在快速发生。最近的报道说,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不及两大央企(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就是明显的例子。应当指出的是,国企的大扩张并不是说国企的强大。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经说过,中国国企只有500大,而没有500强。朱镕基总理设计的“抓大”战略就是要强化国企的国际竞争力。今天国企国际竞争力仍然微弱,“走出去”困难重重 。但当国企在国内市场和民企竞争时,则显得“优势”十足。
有两个特殊的现象引人注目。一是央企化,就是地方政府都拼命想和央企发生关系。与央企结盟是地方的理性选择,通过这种途径,地方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利益,即政策利益和经济利益。很显然,和央企结盟,地方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利益。一些本来通不过的项目,一旦央企卷入,就很容易得到批准。同样,和央企结盟也可得到经济利益,这不仅仅是因为央企本身掌握着大量的资金,而且也是因为央企对中央政府的巨大影响力,通过央企,地方很容易融资。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民企开始想和国企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这有些不可理解。民企和国企发生关系,和国企形成依附性关系,对民企来说,是无可奈何之举。因为说穿了中国还是权力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和国企发生关联是民企寻求政治保护的一种方式罢了。道理很简单,尽管民企有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但宪法和法律仅停留在纸面上。在实际政策领域,民企处处遭歧视。无论民企发展到如何强大,在权力面前都会显得无能为力。一旦权力要处置民企,民企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国有部门并非西方的公共部门。国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掌管国企的个人。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变相的“私有化”,或者内部“私有化”,国企的掌权者或者国企的代理人实际上主导着国企的一切,并且不受任何有效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