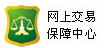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分多次进行,用了4个小时。邓小平的坦率、真诚、客观、冷静以及坚定的信念和敏捷的思维,给法拉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事后说他的被采访“考试及格”。不难看出,这次采访,透过天安门毛主席像、毛主席纪念堂等问题,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如何评价毛泽东功过的大问题。
早在几个月前,邓小平就已看出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他曾对中央负责同志说:“一切都很清楚,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
中央也早在法拉奇采访邓小平之前,在1980年3月,就已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这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曾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
曾参与过《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龚育之接受笔者专访时说,最早提出作历史问题决议,应该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公报认为,关于“文化大革命” “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龚育之回忆说:“《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十一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中央组织了由乔木同志负责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二十来个人吧。陆续有人加入,也有人离开。写作的地方,是万寿路新六所的一号楼。一共搞了无数次稿。这不是夸大其词,是没有法子计算次数。当然,主要的正式的有几次,是可以说得清楚的。”
1980年3月,起草小组经过材料准备、酝酿讨论,提出了一个几千字的提纲。龚育之这样回忆:“这个提纲送给乔木同志,送给小平和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3月15日,乔木同志有一次谈话,谈到《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他认为,现在说‘文化大革命’错了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乔木同志初步地思考了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3月19日,邓小平第1次同主持决议起草的同志谈话,明确提出了关于决议起草的3条指导方针。第一条,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条,是要对解放以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中央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条,就是要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个基本的总结。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4月1日,邓小平又一次对决议起草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提出了决议的整体框架:先有个前言,然后建国后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束语。
1980年6月起草出了初稿,送中央书记处讨论。龚育之感叹:“说是初稿,其实包括多少遍修改,多少次稿子。为简单计,算成第一次稿,初稿。”
6月27日,邓小平谈了对初稿的意见,认为稿子没有很好地体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要求,要进行比较大的修改――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要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书记处讨论的意见,起草小组又重新起草,反复改写。龚育之回忆说:“乔木同志更多地参与到起草过程中来,拿出去讨论的稿子他都要认真修改,不少段落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重新写过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部分。”10月,完成第二次讨论稿,即提交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的稿子。讨论不是集中在北京,而是由中央把讨论稿分发给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分头组织讨论。作为起草小组的成员,龚育之也与其他同志一样还分头到各地方去听取修改意见。
10月25日,邓小平看了4000人讨论的一些简报,简报中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他认为许多意见很好,要求起草小组把好的意见都吸收进来。同时他认为讨论稿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龚育之说:“当时,小平同志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4000人讨论以后,胡乔木提出了起草新稿的原则设想。之后,起草小组又重新改写。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同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认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并对建国以后各段历史做出了概括性的评价。胡耀邦主张决议稿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的意见,邓小平表示赞成。龚育之补充说:“不多久,小平同志又转告了陈云同志的两条意见。一条是加一段话,讲解放以前党的历史,60年历史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就概括得更全面了。再一条是提倡学哲学,学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3月31日发出了第三次提供讨论的稿子,发给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一些在党内工作时间很长、威望很高的老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
根据这些意见,起草小组继续修改,拿出了第四次供讨论的稿子。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70多人参加,讨论了10天。龚育之透露:“曾经决定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来概括毛泽东后来的错误思想。讨论中很多人不大赞成,认为说不清楚,不如就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概括,这样才能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后来在历史决议中就没有再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提法。”
5月19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把各种好的意见吸收进去,又作了很多的修改,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这是第5次提供讨论的稿子。最初交给4000人讨论的稿子是50000字,后来重写过的稿子压缩到28000字。经过吸收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这次稿子是32000字,增加了4000字。龚育之说,从意见的条数讲,恐怕吸收了好几十条。
6月15日至25日,举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进一步讨论决议修改稿。6月22日,邓小平在预备会上又作了重要讲话。在讨论中,中央委员们提了很多修改意见。龚育之回忆,根据这些意见,对决议稿又作了修改,吸收的实质性意见将近百条,篇幅也增加到35000多字。
6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还召开在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共130多人的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
“经过长达1年多(3个年头)的起草过程,经过上上下下反反复复走群众路线的讨论过程,吸收了各种好的意见,拒绝了各种不合适的意见,所谓博采众议,又力排众议(前一个‘众’是大众,后一个‘众’是小众),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一历史决议。”接受专访时,龚育之说到这里时语气不免有些高昂。
“《历史决议》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制定和通过的,集中了我们全党的智慧,但有种观点认为,《历史决议》是一时需要的产物,政治妥协的产物。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对此,龚育之果断地说:“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个决议是科学研究的产物,是全党讨论、民主集中的产物。当然不是说这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科学认识已经达到绝对完善,不需要也不能够发展了,那样的东西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但是我的确认为这个决议是认真的,是根据事实努力用科学态度来对待历史问题的,绝不是简单的一时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龚育之认为,宣传这种观点就为两种思潮开了门。一种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这种思潮下,把《历史决议》说成是一时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就是为了动摇这个决议,以便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成果。另一种是“左”的思潮,认为作决议时的那种情况,困难甚多,积怨甚多,所以着重讲错误,光注意“病理解剖”,结果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重了,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说重了,现在看来否定过多,主张要恢复。恢复什么呢?说到底,就是想恢复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东西。这两种思潮来自不同的方向,却走到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历史决议》不是科学认识的产物,最终想动摇决议。
1981年6月底,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正式通过了《决议》。这是向党的60华诞献的一份厚礼。《决议》以历史的辩证的锐利眼光拨开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这样一个科学命题,在罕见的两难之中做出了一个合实情、得民心、有远见的正确选择。
全会也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早在1980年8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就辞去了国务院总理职务;这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赵紫阳接替华国锋,成为中国国务院第三任总理。
华国锋的职务发生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做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前――1980年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对此,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有具体的论述,同时也肯定了华国锋的功绩:“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众望所归,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全会一致要求推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邓小平谢绝了,提名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后来,他是这么谈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邓小平认为,在60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中央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
邓小平虽然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排名也不靠前,但他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受到了全党的公认、拥护和爱戴。当时已担任党的主席的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说:“……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这些年常委起主要作用的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四位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这不是什么秘密,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候他们还用另外一个词,叫‘主要设计者’。不管哪个词,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告诉全党呢?我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毛泽东。邓小平说:“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沧海桑田,时光飞逝,一代伟人毛泽东缔造的共和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毛主席像和当初开国大典上第一次悬挂时一样,依旧牵动着无数中国人不变的情怀。毛主席那安详的面容、深邃的洞悉一切的目光,依旧注视着我们,注视着共和国的今天和明天!
(本文摘自《邓小平最后二十年》新华出版社 余玮 吴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