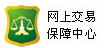【香港《南华早报》6月17日文章】题:受困心态(作者 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相蓝欣)
110年前的6月,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中国媒体最近刊登了许多反思该运动的文章。今年的语气迥然不同。以往曾有人骄傲但有违史实地宣称,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抗击帝国主义的伟大事件。还有人极力赞扬那些号称刀枪不入、能击败蛮夷的叛乱农民。如今,这两种论调都不复存在。事实上,该运动的根源是受困心态,是害怕外国直接干涉中华帝国的内部稳定(尤其是外国不赞成清廷发动政变推翻有改革思想的光绪皇帝),从而引发战争。
中国许多评论人士似乎认为,关键教训是落后就要挨打。有鉴于此,如果想防止中国与西方之间再度发生严重灾难,北京就必须在言语和行动中显示自己的力量。
近年来的两本畅销书表明,一种新的受困心态可能正在抬头。一批民族主义学者、作家和记者共同撰写的《中国不高兴》宣称,中国受够了外国的批评。《货币战争》的作者则是一位业余货币历史学家。他耸人听闻地指责说,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发动了货币战争,目的是破坏中国的经济增长。
在当前形势下,对外关系有两个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令中国和西方感到忧虑。
首先是缺乏透明度。具体表现是:决策过程往往笼罩着重重迷雾;茌对外部世界发布信息时,中国使用的措辞含混晦涩。“和平崛起”和“和谐世界”的概念都没有得到接受,因为全球受众渴望知道中国对10到20年后世界形势的构想,却没能如愿以偿。中国有着什么样的军事发展战略?打造远洋海军的目的何在?中国如何展望世界经济?中国当前希望展示何种形象?这是大多数外国人脑海中的疑问。
其次,中国不善于解释本国真正的问题。中国官员正确地认识到,优先要务是解决国内问题,外部关系应该为这个目的服务。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纵观中国历史,所有统治者面临的最大挑战都是保持国内稳定。无论是城市国家(如新加坡)还是小岛政权(如台湾)都不必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问题包括富裕和贫困地区的发展差距,收入分配不均到了危险的地步;这个儒家社会本该重视教育,但教育制度却是失败的;社会不安定的现象广泛存在;当然还有与少数民族的复杂关系。
北京试图把内部事务与外部事务联系在一起,但往往以不必要的防御态度和抽象语言为自己辩解。症结在于中国的决策机制中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其决策程序仍然保留着斯大林主义的许多特点。比方说,中国意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热心向世界其他国家推销儒家文化,但宣传机器仍然要求党内精英重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尽管许多党内精英忙于捞取资本而没时间阅读《资本论》,但社会下层民众在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却越来越多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因此,如果北京无法说服全世界相信,保持国内稳定对所有中国人(而不光是精英)有益,那么减轻国内压力的另一种方案就是归咎于外国的影响。这种新的受困心态也许更危险:恰恰因为中国正在恢复经济实力,所以给极端民族主义提供了肥沃土壤。中国政府可能会蒙受更大的压力,不得不盲目以“强硬态度”对待西方,无法成功说服全球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