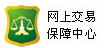【美国《华盛顿季刊》2011年冬季号(提前出版)文章】题:对付一个自相矛盾的中国(作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
人们在回想2009年和2010年的时候,会将这段日子看成是中国让世界越发头痛的时期,因为中国对许多亚洲近邻、乃至美国和欧盟,都作出了越来越强硬、越来越好斗的举动。就连它与非洲和拉美的关系都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紧张,最终导致中国的国际形象自2007年以来开始走下坡路。假如这种朝着自信与傲慢方向的偏转是一种相对长期的、根本性的趋势,那么其他国家该如何应对呢?
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的新姿态是其国内激烈辩论的产物,代表了倾向于保守和民族主义的势力目前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即要实现政策强硬化,并有所选择地展示国威。中国国内眼下看似态度统一,但其实依然是一个内部矛盾性突出的崛起中大国,具有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国际属性。目前,许多新的声音和因素正参与到空前复杂的外交决策中来。因此,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往往多种多样,且彼此矛盾。理解这些相互矛盾的属性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预测北京将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其越来越具矛盾性和多面性的举动。每一种政策思潮都会给美国及其他国家带来不同的政策影响。
中国显然存在不同流派的思想与分析,或者说存在不同的思想与分析“倾向”。在各种相互矛盾的国际属性的影响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于是同时显现出多种因素的特点。例证就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这一官方政策。虽然这一政策所包含的多种取向性明显不同,但它们彼此间并不一定会互相排斥。
笔者在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进行接触、阅读这些人著作的过程中,发现有七种思想比较突出。从最左端的孤立主义倾向到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机构的最右端的思想,这些理论覆盖面非常广。
从单个的角度来说,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位于最左端的“本土论”的存在,认识到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抬头,但这股影响力同样不应被夸大。套用中国人的话说,这一流派“雷声大、雨点小”。
“现实主义论”则影响了中国绝大多数精英,占据了中国现今国内辩论的重心。
“大国论”对于美国而言相当于一张暗藏的王牌。从经济发展到政治稳定,从地区安全到台湾问题,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言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不愿——也不去寻求与美国的敌对关系。幸运的是,这一流派的大多数支持者是政府官员。虽然这些人既不相信也不喜欢美国,但他们都足够务实,认识到美国对中国许多国内、地区和全球目标所具有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亚洲优先论”的拥护者们则有许多工作要做了。中国的地区关系——从对日到对韩,从对东盟到对印度——近几个月来屡遭重创。这对美国而言也许是个好消息,因为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努力加强美国同中国所有周边国家的关系。
至于“全球南南关系论”,华盛顿就需要认清北京玩得非常娴熟的那套把戏了。中国在非洲的运作令美国相形见绌,在亚欧大陆的活动正在发展,在中东和拉美的交流也越发活跃。美国应当认识到,与中国在全球影响力方面的竞争刚刚开始,美国应当增加在世界各地的运作与外交活动,与北京争夺上述“中间地带”,争取“中间大国”。
对于“选择性多边主义论”,美国必须明白这一学派倡导的是以实现自我利益为目标,有策略性地、有所选择地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并不认同全球自由秩序的许多前提条件,即使中国从这种秩序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不是出于任何更高层次的思想义务。
最后,华盛顿必须认识到,位于各派思想最右端的“全球主义论”已经输掉了中国国内的辩论,这一流派的声音从2008年开始就沉寂下来了。中国继续采取基本上“坐享其成”的态度,对全球治理做出的贡献仅仅维持在足以转移西方批评的水平上。虽然必定会增加中国的猜忌,西方依然应当继续敦促北京拿出更多行动,继续公开揭露其最低限度的贡献,但同时也要降低对这个自私狭隘的国家的期望值。当然,华盛顿还是要在牵扯中国利益的问题上,吸引北京开展有选择性的跨国合作。
此外,上述思想流派同样对政策具有整体性影响。国际社会必须明白,中国的国际属性并非一成不变。它正处于变化当中,是一件半成品,依然具有争议性,一直处于辩论的焦点。就此来看,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有能力通过行动和言语来影响正在进行中的辩论(以及辩论的政策结果),而且影响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
美国的严厉言辞与强硬行动很可能在中国造成一种强化性效果,导致北京作出更加好斗、更令人担忧的举动,因为国内的声音会怂恿政府与美国作对。然而另一方面,如果采用相对安抚性的言辞,鼓励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深入参与全球治理,那么同样会加深中国的猜忌,不太可能达成美国希望的结果。因此,美国和西方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对华强硬态度很可能导致中国的回应变得更加强硬,但是安抚性做法只会强化“现实主义论”者的 “中国优先”倾向。